「其實我覺得家族治療(如附註)四個字,就是讓我的媽媽爸爸能夠有效溝通,這樣就好,很簡單的。」許多家庭在面臨問題時,選擇隱忍或逃避,而非坐下來一起面對。家族治療以解決伴侶、夫妻、家庭成員之間的困難為主,陳家子女因擔心母親無法與家裡成員溝通,選擇全家一起來諮商,希望透過諮商心理師(以下簡稱心理師)的引導,慢慢築起他們與母親的橋樑。
註:以往諮商與心理治療各理論派別皆以個人為治療對象,家族治療(Family Therapy)是以當事人所屬的整個家族系統為治療核心,並探討其家庭成員彼此的互動模式。資訊來源:社團法人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協會網站http://www.acft.org.tw/qSynopsis.asp
「心裡的話還是要一個出口。」
【專題記者徐卉馨、吳佩容、范莛威、林莉庭綜合報導】陳家有四個孩子,為改善父母關係選擇接受家族治療,他們在諮商過程中,發現母親長期以來不表達自身的想法,與父親性格有關,「主要是因為父親比較保守,是大男人主義。」陳三弟感受到母親並不快樂,希望透過溝通,讓母親逐漸願意敞開心房。

家庭成員一同聚在諮商室,透過心理師的引導,找出解決家庭困難的方法。 圖/范莛威攝

小真(圖上)和芒果(圖下),兩人大學都修讀心理輔導相關學系,也曾一同接受伴侶諮商。 圖/徐卉馨攝
引導出新角度 理清家人互動的千絲萬縷
個別諮商著重個人的深沉感受,當一位案主說出一段話時,無法體現這段話在「關係」中的意義。家族治療是一種對話的練習,也是溝通的功課,關注以案主為核心的家庭成員,以系統的觀點來分析家庭成員關係,並釐清衝突背後的脈絡,而普遍的形式為家庭成員或伴侶一同與心理師會診,注重彼此的溝通、互動模式。
當嫌隙與爭執磨損親密的伴侶或家庭關係,溝通的橋樑未能搭建起來,關係便無從改善,此時家族治療可作為尋求關係改善的一項管道。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、心理師羅惠群說:「要轉彎才能避開情緒。」心理師會轉換說法,以紓解家人間互相究責、羞愧的情緒。
心理師進行家族治療時,也需同時分別觀察家庭成員的表情、肢體動作,以及成員之間的互動。芒果指出,進行家族治療的心理師需同理各成員心中的疑慮與憂心,並在言談間協助成員理解彼此內心的真實情緒。
盼心理諮商所所長、心理師呂伯杰也說明,心理師要顧及不同人的感受,並隨時觀察這段關係的動向,當發現對話無法繼續進行,心理師應試圖點出卡關原因,以提供案主新的視角與觀點,避免在看似無解的狀態裡停滯不前。社團法人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協會(以下簡稱華家)理事長、心理師徐森杰解釋心理師的角色,「去協助這個家庭看到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。」心理師經由適時引導,能讓案主摸索出合適的互動方式,並能共同面對彼此的關係。
徐森杰坦言,家族治療實為創造出一個溝通平台,「家族裡面的人可以彼此交流內心話,改變對彼此的看法。」華家副秘書長、心理師黃子銘也認為,家族治療提供家庭聚在一起討論事情的契機,使家庭關係變得更緊密,他說:「我覺得家庭諮商有點像是開家庭會議,大家一起來看家裡發生什麼事情,然後我們一起來想辦法。」
在親密關係中,人們反而更控制不住宣洩情緒、說出傷人的話語,對話過程不免產生衝突。呂伯杰將家族治療的現場比喻為菜市場,與個別諮商相比,家庭成員之間更常出現語言衝突的情形,心理師需依狀況適時介入家人的對話。呂伯杰舉例,曾有一對前來諮商的夫妻,妻子保持沉默,而丈夫激動時會以情緒性語彙攻擊對方,他便適時提醒案主對話已落入動彈不得的瓶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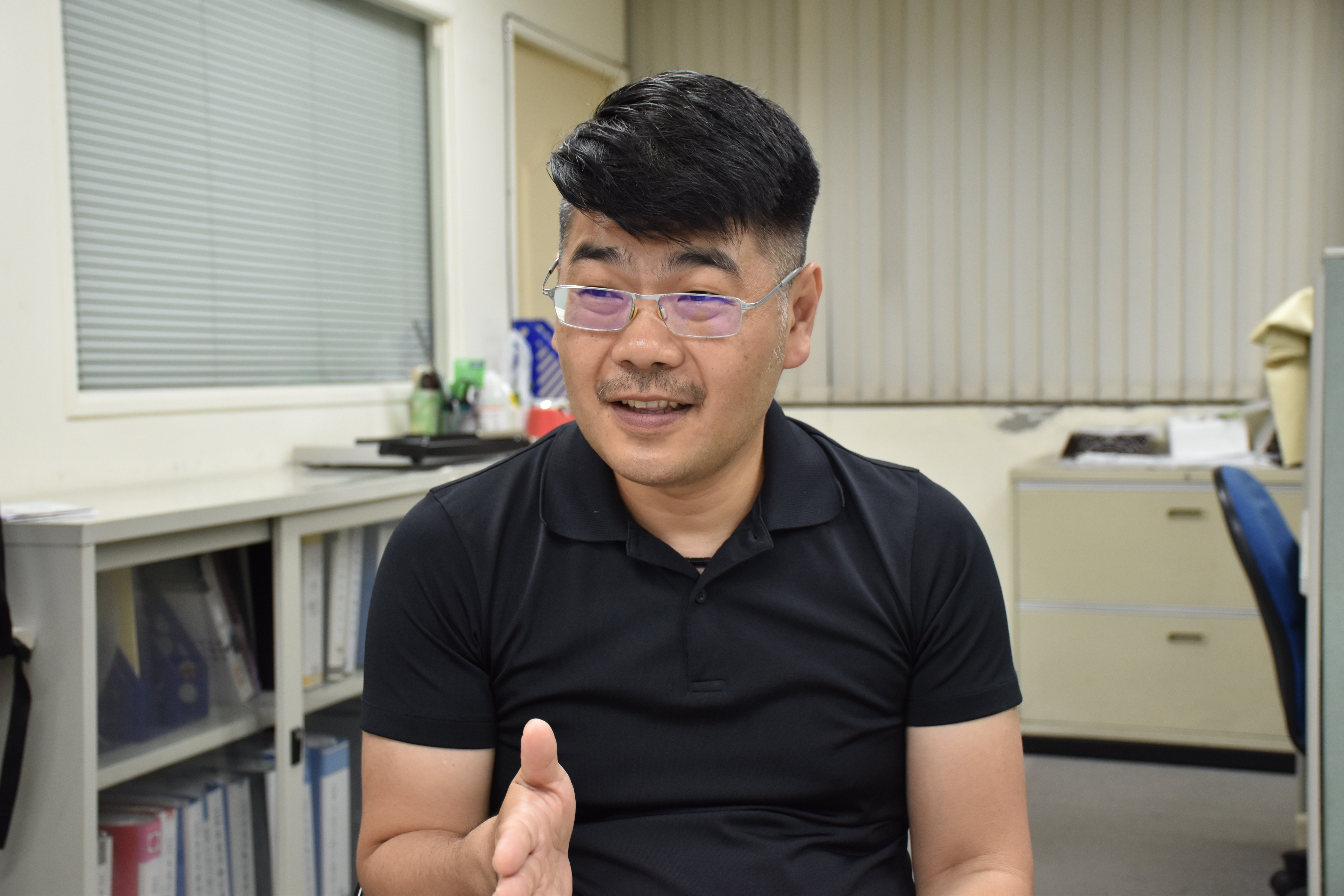
徐森杰為社團法人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協會的理事長,除提供諮商服務外,同時也培訓新的心理師。 圖/范莛威攝
把自己顧好再去顧別人 心理師的家庭作業
黃子銘自身接受過伴侶諮商,「那時候印象很深刻,我以為我講得很清楚,結果沒有想到我太太完全誤解。」在兩人對話沒有共識時,心理師慢慢說服雙方耐心聆聽與思索,再說出自己的理解,讓兩人意識到彼此的誤解。
談及接受諮商的感受,黃子銘說:「我的感受是覺得被理解、被聽懂、被看見,是很溫暖的。」他也認為諮商過程像樂器調音,是調整跟修復的功夫,心理師用陪伴慢慢調整案主的思考方向,並協助案主修復內心的創傷,「是一個靈魂跟另外一個靈魂相遇。」

心理師在關係中也會遇上困難,黃子銘在婚前與伴侶一同接受過諮商。 圖/范莛威攝
不了解家族治療 難以在社會推動
針對家族治療推行的現況,呂伯杰分析,主動尋求家族治療的伴侶或家庭寥寥無幾,案主多半經由心理師、輔導老師或社工轉介才接觸到家族治療。蔡春美也指出,目前各大心理諮商中心都有相關資源,心理師也會提供轉介管道,但若民眾對家族治療不了解,則不會主動尋求,那麼管道多寡其實並非影響推行的重點。

呂伯杰為盼心理諮商所的所長,認為民眾對於家族治療還不了解,故較少向外尋求協助。 圖/范莛威攝
缺乏教育資源 培養心理師的難處
台灣現行制度下,心理師分為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,根據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》,心理師首先必須在諮商心理所、系、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,且實習至少一年、成績及格,並具有碩士以上的學位,才能參加心理師考試,而通過考試後,將由衛生福利部發放證照。
而只要取得心理師的證照,便能進行家族治療,但許多心理師缺乏家族治療實務經驗。林麗純分析,獲取證照的心理師不一定具備執行家族治療的能力,心理師考試引導了教學,現今有些大學開設家族治療相關課程,「可是這是選修的,因為考試不考。」羅惠群也指出,台灣目前沒有發放家族治療師的證照,心理師通常自行標明專長項目,如此民眾在選擇心理師時,才可以透過心理師的學歷、專長領域來選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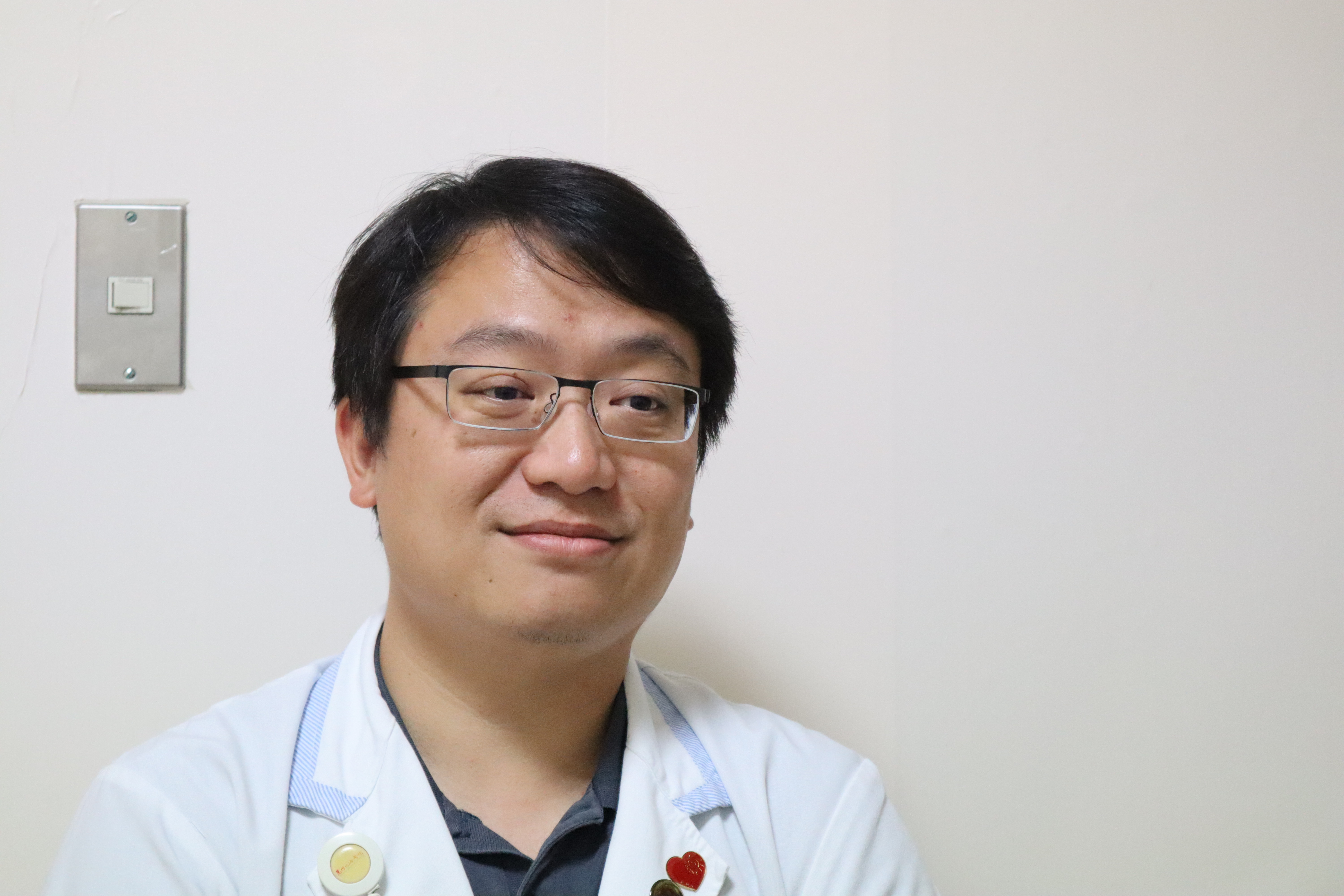
心理師羅惠群目前任職於馬偕醫院的協談中心,提供的諮商項目包含家族治療。 圖/徐卉馨攝
家族治療,是家庭渴望理解彼此的過程
如何判定需要被治療的條件?徐森杰說:「華人文化裡面的儒家思想,把我們非常多人綁得死死的。」他說明,當今台灣社會仍存有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兄弟友愛等傳統價值觀念,「治療」對於多數人來說仍是沉重的名詞。
其實參與家族治療對於許多案家來說並非狹義上的「治療」,陳大哥說:「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去『治療』的,以治療這個詞來說的話。」他指出,小時候父親不擅言詞,時常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對待他,比如以體罰的方式教育他,且缺乏給予讚美,「但我相信不是我的父親這樣而已,這是台灣人的通病。」
而對家族心理師來說,家族治療是一個平台,讓家庭中每個人內在的需求可以被其他家人看見,徐森杰說:「我覺得家庭是一個有愛的地方,可是家庭也是一個帶來很多痛苦的地方。」他認為,家人會互相在意是因為對彼此有愛,才願意互相承擔,而心理師的角色就是去協助家庭發現真正適宜的互動模式。
家族治療在現今的台灣社會,依舊有許多偏見需要被克服,多數人仍認為參與家族治療是小題大作或丟臉的行為,但對案主來說,家族治療不僅是解決溝通困難的管道,也是家庭成員渴望更理解彼此的過程。
